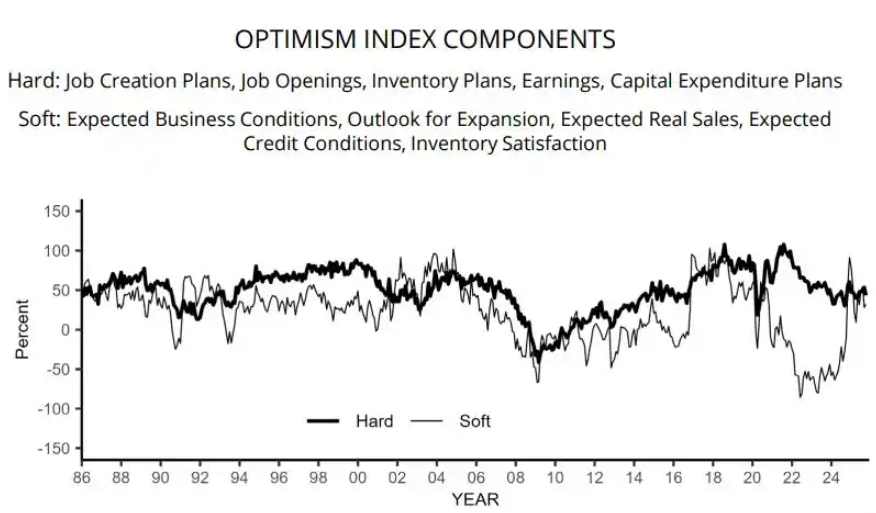1967年的夏天,十四岁的来子到了联社大院。大院是手工业联社集中了好几个小企业的地方,来子在草织社上班。
草织社,就是将稻草做成床垫、草绳,草袋子,将荆条做成荆巴、箩筐的手工业企业。来子在脚踏草绳编织机前工作。要用一只脚反复用力踩着,机器才会转起来,一双手要不时往入口处添加稻草,如果添加得太多,会把入口卡死,添加得太少,草绳会变细不合格。
外面树上的知了“命命嘛~命命嘛~”的叫个不停,乌烟瘴气的厂房里没有任何降温设备,闲人都会闷热难耐,更何况来子才十四岁,个子又比同龄孩子矮了一截,在草绳机前手脚并用,一会功夫便是浑身大汗。草绳机是靠脚踏惯性旋转的,速度慢了反而会更加费力,想偷懒都难。
宋主任来检查工作了,他是草织社的负责人,身材魁梧,脸色黑黑,平时表情极其严肃。已经累得昏头涨脑的来子见宋主任到来,便停下了机器,向站在身后的宋主任提出了要求:“宋主任,这活太累了,我实在干不了,能给我调换一个活吗?”
“什么!还要调换工作?你是怎么来的你还不知道吗?”
一听这话,来子无语了,只好转过身来继续手忙脚乱,确实,他来到这里上班,有点不正常。
靠挑动族群斗争、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后,执政者对这个杀手锏爱不释手并屡试不爽,把国人分成了三六九等,到了1966年,对这个图腾的崇拜达到了高潮。
来子家庭出身不好,属于“黑五类”家庭,他本人属于“狗崽子”,说好听了叫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,他也想和那些同龄人去串联,加入造反派组织在外面造反,只因为是“狗崽子”没人敢接纳。外加来子的家庭经济拮据,也急需挣点钱贴补家用,来子便将眼光盯在了劳动调配站的安大哥身上。
安大哥二十多数,是劳动调配站的工作人员,负责向一些企业推荐介绍劳工,除了社会闲散人员之外,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部门和这个人。
只要有时间,来子便会去调配站,和无所事事的安大哥聊天说话,或用低级的棋艺陪安大哥下象棋,久而久之,安大哥便成了来子的朋友。一天,正在下棋时,来子终于说话了:
“安大哥,求你个事呗?”
“嗨!来子,啥事呀?有事和我还用说求?”
“我家的情况你都知道,我整天这样呆着也不是长法,你给我介绍一个工作呗?”
安大哥手中拿着棋子,疑惑的眼睛盯着来子:
“你不是开玩笑吧?你才多大啊?你瞧你那个头?”
“我说的是真事,不是开玩笑,我家里生活困难,我真想找点活干帮我妈挣点钱”。
没等安大哥说话,来子又接上一句:“如果上班了,到了星期天,我还会来这里和安大哥玩”。
安大哥沉思了一会,推开棋子:“既然这样,好吧!那边的手工业联社的草织社正好在要人,我把你介绍到那里吧!”
当天,来子便拿着介绍信来到了草织社,把介绍信交给了宋主任。宋主任手拿介绍信便问:“好啊!真介绍来了!那人来了没有?”
来子抬起头看着宋主任说:“宋主任,就是我!”
“什么?别开玩笑了!我要的是干活的人,我不要小孩子!”
来子满脸无奈地拿着介绍信回到调配站,把宋主任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安大哥,安大哥听后,自信地笑着对来子说:“你再去草织社,告诉那个老宋,就说是我说的,这个人你要也得要,不会要也得要!”
来子见到宋主任后,把安大哥的话又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宋主任,宋主任听后,脸上显出一脸无奈和苦笑:“什么?要也得要,不要也得要?他真是这么说的?”
“是!安大哥就是这么说的!”
“哟!还安大哥安大哥的?得!我算是明白咋回事了,行了,那你就在这干吧!不过,丑话我得说在前头,我不管你安大哥不安大哥的,你来了就得和别人一样干活,我这里可不白养活人!”
打草绳的活,再累也要坚持下去,不能给安大哥丢人,也不能让宋主任看不起,这是来子唯一的想法。
时间长了,来子了解到,滦河手工业联社下面有好多企业,仅在大院里就有草织社,木工社,铁工社和皮麻社,在滦河街里,还有缝纫社,白铁社,统归承德市二轻局管辖。
铁工社靠近大门,那里是打铁的地方,鼓风机整天嗡嗡响着,扁担式的电动铁锤,据说是技术革自己发明制造的新设备,砸起烧红的铁块,“咣!咣!”的巨响,满滦河街都能听到。铁工社的老师傅和徒工们,基本都是傻大黑粗,脸是黑色的,衣服也是黑色的,只有一口牙是白色的。
木工社在大院最里面,除了开电锯时有巨大的声响外,平时也难得清静,锯木、凿眼、推刨子,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断。但木工社的师傅和徒工们,都比较干净利索,上班时身上除了围裙上粘些锯末外,衣服都很整洁。
最清净的地方是皮麻社,一切工作都是静悄悄的。那里除了几个老师傅之外,没有年轻人,因为年轻人宁愿学木匠、铁匠、缝衣匠、白铁匠,也不愿意去学臭哄哄的皮匠。
在宋主任的眼里,来子也并非一无是处,每天上班开工前,“雷打不动”,大家站在一起,拿起“红宝书”学习的时候,来子在读“语录”,读“毛选”时就有点用,此时的来子也多少能找到一点自身价值。
来子岁数小,觉多,晚饭后就犯困,但每晚也必须参加“雷打不动”的活动,全社一起学习、批判。学习“毛选”,学习上级文件,实在没事了,就批判被揪出的几个坏分子。
认识李永存,是来子头一次参加在木工车间大厂房里进行“雷打不动”活动的晚上。五十来岁的联社刘主任宣布开会,随后便将主持会议的权利交给了一个年轻人。
年轻人站了起来,清清嗓子,表情严肃地高声说道:“全体起立!”
众人应声从坐在木工房架子上,木板上,半成品的棺材里站了起来,掏出“红宝书”。
年轻人右手举起“红宝书”挥动着:“首先,让我们共同敬祝,伟大领袖毛主席······”
众人也举起“红宝书”向前挥动:“万寿无疆!万寿无疆!”
年轻人:“祝愿林副主席······”
众人:“身体健康!永远健康!”
呼完口号后,众人坐到原来的地方。
年轻人: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!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,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绘画绣花,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。今天,我们继续对联社的阶级敌人进行批判!五类分子,站起来,到前面来!”
话音刚落,便有几个佝偻着腰的人从不同的地方站了起来,走向年轻人所在的“前边”,来子数了数,一共是五个人。年轻人喝令他们站成一排,又喝令他们弯下腰,双臂翻到后边,这是流行的“喷气式”。
随后,便是几个人上来,轮番数落这几个人的罪状。
趁着上面人大喊大叫,来子悄悄地问身边的侯哥:“侯哥,那个年轻的是什么领导?”
侯哥低声说:“他哪是什么领导啊?他叫李永存,是一个还没出徒的徒工!”
“那他为什么比刘主任还厉害?”
“他呀!我们是师兄弟,他对木工手艺不太在意,不过,这家伙政治立场坚定,能说会道,还根红苗正,是红五类,从文革开始,这家伙越来越能耐了,能揭发人,还造了师傅的反,揭发他师傅往家偷木板,现在正造刘主任反呢!没看吗?刘主任都快被夺权了!”
来子通过揭发批判那些人的发言才知道,那几个阶级敌人,有一个是解放前的“一贯道”点传师,另外四个人,都是解放前家里有手工业作坊的“资本家”,公私合营后进入联社的,眼下联社好多企业,解放前都是这些人得家族买卖。
批判会结束后,李永存做了总结讲话:“批判会我们开过多次了,但联社的坏人绝不是这几个人,联社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是没有揭开,很多人对批判会态度不积极,难道想当逍遥派吗?我正告你们,不革命就是反革命!”
也许是因为联社的人大多是老街坊老邻居,世代都生活在滦河街的缘故,批斗会的气氛并不热烈,除了铁工社的铁匠张怀等几个少数人之外,多数人表现冷淡,对几个阶级敌人不是特别愤恨,这让李永存很恼火,尽管后来的批斗会在李永存的指使下,张怀等人将沉重的大牌子用细细的铁丝挂在阶级敌人的脖子上,做深度弯腰,双手在后面高高的翘起,做“喷气式”俯冲,但革命气氛仍旧不见高涨。李永存批评这种现象是传统手工业者脱不掉小农思想,也是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的巨大差别,因为此时附近的承钢,“站派”和“坐派”的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荼,武斗很激烈,壮观,那才叫革命!
没有多久,终日小心翼翼又忐忑不安的刘主任,终于进入了阶级敌人队伍,这下,批斗会上发言的人就多了起来,气氛比原来激烈很多。有人谴责刘主任曾经扣罚过他的工资,有人声讨刘主任没有及时给他涨工资。李永存拿出了经过查账找到的证据:去市里办事,刘主任在报销的每张五分钱一张的车票上,出现过两个号码连着的车票,一个人怎么会买连号的车票?这分明是给亲友代买了车票,或捡别人的车票拿到联社报销,是典型贪污行为!
刘主任的民愤比几个老牌阶级敌人大,所以受到的待遇也比较高。除了享受那几个人的待遇之外,几个对刘主任不满的人,将刘主任双手的大拇指用细绳绑上,吊在房梁上抽打。来子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张怀在获得李永存首肯的情况下,用绳子捆绑刘主任的双臂,只见张怀将膝盖顶在刘主任的肩上,双手用力,随着张怀上提绳索,刘主任低沉的“哼”了一声,便面色惨白,大汗淋漓,晕倒在地上。
晚上的活动,让来子认识了很多人,除了几个比来子大上几岁的学徒工之外,来子还注意到,联社还有一个姓付的副主任,同时也是皮麻社的主任。付师傅平时话语不多,为人沉稳,但说起话来很有分量,不知为什么,连李永存这样的青壮派,对付师傅也是礼让三分。
也正是因为参与这些活动,岁数很小个子又矮的来子,也引起了联社众人的注意,但来子引起别人关注,并非是因为有什么过人之处,相反,倒是因为他出的几次洋相引起的。
来子岁数小,白天干活又疲惫至极,到了晚上就犯困。当参加晚间活动的时候,他经常找一个背静的地方坐下,如果场上没有特别让他感到兴奋的内容,他便怀里抱着一把手电筒,静悄悄地在偏僻的角落里,人不知鬼不觉地睡了,并且睡得很死,经常在散会以后,他还一个人在角落里沉睡着,如果没有人去惊动他,他便会一直睡到天亮。很多时候,都是最后离开会场的人去叫醒他,他才会睡眼惺惺,里倒歪斜地走回家。
这一点也被李永存发现了,他很不满意这个小“狗崽子”的表现,当着众人面训斥过来子,但来子睡觉的坏毛病并没有因此改变多少。后来晚间活动时,李永存干脆就告诉来子,不得坐在角落里,必须坐到第一排。
第一个洋相就出在第一排的位置上。那又是一个批判会,会场中央刘主任等阶级敌人挂着牌子在做“喷气式”,照旧有人发言批判,这些情况已经引不起来子的注意,困劲又上来了,因为第一排不能躺下睡觉,他只好强打精神看着前面,时间不长,来子眼皮耷拉下来,头也点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,来子被一片笑声惊醒。
待他醒过来之后才发现,自己已经倒在了那几个做“喷气式”的人脚下,原来,来子先是点头瞌睡,后来就抱着手电筒一头扎在了地上,脸上沾满了灰土,活生生的像个京剧大花脸,引得全场人哄笑,连那几个痛苦不堪,挂牌子做“喷气式”的阶级敌人们,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另一次出洋相,就带有几分恐怖了。那天活动是听中央文件,地点选在木工车间厂房,里面有很多半成品棺材。平日里,来子见到棺材就有几分胆怯,但由于那晚人多,再加上别的棺材里也坐着人,来子便找到一个空棺材坐了进去,借着棺材头部倾斜的地方,来子便靠在那里,没有多久就睡着了。
秋季的夜晚,气温逐渐下降,不知睡到什么时候,来子被冻醒了,当他醒过来之后,搞不清自己睡在什么地方,就慢慢地回想,记得是开会,还想起自己好像睡在棺材里,一想到这里,来子头皮发炸,连忙打开手电看看周边,不看还好,一看才看清,自己果然躺在棺材里!
说来凑巧,院子里值班的人因为看到木工房里有亮光,便拿着手电来到木工房。这边的来子,慌慌张张地从棺材里往外爬,见到了厂房外有人,感觉如同脱离了阴间地府,便快速追上去,那边的人,看到棺材里钻出一个人奔向自己,吓得转身便跑。就这样,一个前面跑,一个后面追,到了灯光下,被吓得哆哆嗦嗦的值夜班人才看清楚,棺材里出来的人原来是来子!顿时坐在地上,哭笑不得。 来子睡觉出洋相的故事,再次被添油加醋地再次传遍联社。
一段时间下来,打草绳、编织草袋,缝草垫子这些活,来子很快就掌握了,但他对篾匠早就不感兴趣了,他觉得篾匠技术含量很低。他想学木匠,想和那些比他大几岁的木工学徒一样,戴着围裙,双臂戴着套袖,身上沾着几片刨花,耳朵上夹着一只铅笔,如果有朝一日,能做这样的小木匠,看起来很精神也很体面。
通过侯哥,把这个意思捎到了木工社张主任那里,侯哥对来子说,张主任对来子印象还不错,但眼下社里还没有招徒工的计划,等明后年招徒工时,来子岁数也差不多够条件了,那时候可以考虑。
为了顺利实现当木匠的愿望,来子向侯哥和侯哥的师兄弟们要来了淘汰的刨床,凿子,锯等好几件工具,并经常向他们请教划线、合缝、凿卯、割隼等基本技能。在侯哥的指导下,亲手做出用一块整木板加工的,能打开再合上的马扎,接着,又做出了一把椅子,包括下料,划线,严缝,凿卯等所有工序。
就在来子信心满满地预想走向小木工之路的时候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一天上午,来子在去厕所的路上,碰到了付师傅。付师傅见到来子,就停下了脚步,待来子走到身边时,付师傅低下头和说话了:“小来子,我问你个事”。
来子讶异地抬起头望着付师傅:“付师傅,啥事?您说”。
“你在草织社那边,给你多少工资?”
来子回答:“我是徒工待遇,每月二十元,外加两块钱伙食补助,一共是二十二元”。
“你愿意到皮麻社上班吗?”
来子想到皮麻社那边的臭气熏天,想到那边几个老师傅的死气沉沉,又想到即将实现当体面小木匠的理想,就低声说:“付师傅,我想学木匠”。
“孩子,我不强迫你,你先听我说。你别看皮麻社不起眼,没人愿意来,说实话,看不好的人我还不要呢!这边虽然脏了点,臭了点,但皮匠也是一门手艺。你如果来我这,我和你签订合同,你就是合同制学徒工了,学徒工资也比别的地方高,我每月给你二十八元,怎么样?”
二十八元?这对十四岁的来子来说,是个不小的数字!每月拿这些钱给妈,妈会多高兴!
“真的啊?行!付师傅,我去皮麻社!”
俗话说,臭皮匠,臭皮匠。皮匠确实和臭字分不开,臭就臭在沤皮子的池子里。生皮革要放在池子里浸泡,将皮革泡软,将脂肪泡嚢,浸泡时间久了,必然发臭。
来子就从给池子加水开始,进入了皮匠行列。池子边有一个手压洋井,装满一池子要好几吨水,那口洋井出水量不足,压得快了,把手会反弹回去,只能顺着流量,慢慢地压下去。用了一小天的时间,双手磨起了水泡,来子才把水池加满。
接下来,逐渐参与刮皮子,割皮绳,打麻绳,熟皮子,做鞭子,割鞭梢,拉筒皮,进而制作其它车马挽具。来子是苦孩子出身,能吃苦,也很灵巧,学什么像什么,进步很快,付师傅也十分喜欢来子。
活虽然累了点脏了点,但皮麻社的工资待遇还算不错,让来子更高兴的,是他也可以打针吃药不花钱了,有了这个待遇,家里卧病在床的父亲可以吃到不花钱的药了。另一个外人不知道的福利,是皮麻社的人可以得到很多猪油,要知道,当时猪肉和猪油该有多么珍贵,每个月供应的半斤猪肉,凡是去买肉的,都要从那可怜的半斤肉里,尽可能得到更多的油水。
这和皮麻社完成加工猪皮任务有关。按当时的经济计划,屠宰场每天要向皮麻社上交十张猪皮,皮麻社负责简单加工,腌制后,上交市皮革厂。
市场一等猪肉的价格为每斤0.92元,二等猪肉每斤0.78元,三等猪肉每斤0.66元。越是肥的肉等级越高。屠宰场送给皮麻社的猪皮,一等猪皮价格每斤1.20元,因为肥猪的猪皮都是一等猪皮,所以,屠宰场在剥肥猪皮时,为了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,会厚厚地剥,带上一层肥肉,因为肥肉与猪皮一起卖,比单卖猪肉贵很多。
来子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工作,就是去屠宰场验收猪皮等级,确定猪皮重量,回来后,将合在一起,里面很干净的猪皮,在案子上摊开,用片刀将猪皮上附带的肥肉,一片一片地片下来。质量好又干净的肥肉,每天至少有十余斤。这些肥肉,按顺序,轮流由大家拿回家熬猪油,每个人大约一周多就会轮到一次,这是其他单位非常羡慕眼馋的事情。
皮麻社还有一项福利——吃猪尾巴。因为每张猪皮上都带着一根猪尾巴,每天要割下十根。开始的时候,每天把猪尾巴连同肥肉,交给轮到的人拿回家吃。到后来,猪尾巴吃得太多了,家里人都吃腻了,没有人稀罕带回家了,就干脆放在社里,时间长了又怕坏了可惜,所以,攒到两天二十根的时候,就一起加工一次,开水烫掉猪毛,洗干净后放到锅里炖熟,大家随便吃,再后来众人也吃腻了,但扔了又觉得可惜,就送给木工社的,或铁工社的人,无偿让他们解馋。
大门口有一间值班房,联社院里夜间没有配备更夫,由各个单位的年轻人轮流值班,自带行李,每次值夜班三天,由革委会成员带班。来子已经是合同制学徒工,理应尽值班义务。
来子在值夜班时才发现,已经升为革委会副主任的李永存,为革命工作操劳着实不易。夜深人静,大院一片漆黑时,李永存经常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,或书写材料,或看上级文件。
每当此时来子在那里经过的时候,会不由得想起那首歌的歌词——“毛主席窗前一盏灯,春夏秋冬夜长明,伟大领袖窗前坐······”,尤其当李永存肩上披着外衣,走出房间在院子里像伟人一样踱步的时候,来子心里更会油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,他感悟到,毛主席、李永存、张怀,这些共产党人确实与众不同,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,怎么会有如今热热闹闹的世界?
有一次,李永存还拍拍来子的肩膀,主动和来子说话,亲切地安慰来子“不要自卑,你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,我们造反派不会抛弃你们的!” 这让来子受宠若惊并倍感温暖,因为此时李永存的位置和气派,连他的师父师叔和师兄弟们,都难得获得这种待遇。
也正是值班期间,来子发现,李永存的革命工作,也包括找女人,那女的来子认识,是缝纫社的大美女,很多人追求她,但李永存很轻松就得到了她。作为小皮匠的来子只明白一个理儿,闹革命确实值得,他们能得到想要的所有东西,包括职务,风光和美女。
中苏关系紧张,战争好像随时爆发,“备战备荒”,“要准备打仗”,“深挖洞广积粮”,是喇叭里,文件里经常出现的字眼。现实中的紧张气氛也到处可见,滦河到滦平的公路两旁,每隔不远处,便会见到一个圆圆的土堆,在土堆上部装上一个小号铁皮烟筒,远远看去很像一辆辆坦克车停在路边,来子搞不明白,这是吓唬中国人还是吓唬苏联人用的。但“深挖洞”应该是有用的,据说挖了洞,敌人的炸弹就炸不死人。
革委会安排,要在联社院子里挖几条一人多深的沟,上面用木板和泥土覆盖,这些东西能不能挡住空中掉下来的炸弹,来子不清楚,也不敢多问,他只能和其他师兄弟们一起挖沟。联社院子地下,全部是沙土,当土沟挖到一米多深之后,两侧的沙土便会坍塌下来,为了达到一人多深的要求,只好加宽土沟的宽度,即使这样,塌方也经常发生。
一天上午,来子和几个人又被调来挖沟,侯哥和来子在同一条沟里,这条沟深度已经快达到要求了,侯哥挥铁锹的地方离来子不远。就在来子用铁锹从沟里往外扬土的时候,忽听得身后“轰隆”一声闷响,来子连忙转过身来查看发生了什么,这一看,来子惊呆了,原本侯哥干活的地方尘土飞扬,土沟变成了深坑,塌方了,侯哥不见了!
来子爬上地面高声大叫:“快来人啊~~塌方了!侯哥被埋了!”
大院里的人应声从各个车间跑出来,奔向掩埋侯哥的地方,很多人等不及领导指挥,直接跳下深坑,在来子确认的地方,用双手挖土,先下去的人双手挖出血后,后面的人再跳下去接着挖,所有在场的人都焦急万分。
十几分钟后,人们发现了侯哥的后背,围观的人们一阵惊叫,再继续一会后,终于把已经停止呼吸的侯哥全部挖出来了。抬上地面后,有明白人立即给侯哥做人工呼吸,过了一会,侯哥活过来了,睁开了眼睛,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,有人说侯哥身体好,也有人说侯哥命大。
一直让李永存纠结的,揭不开联社阶级斗争盖子的问题,终于出现了转机。李永存以他敏捷的政治眼光和锐利的物理眼光,发现挂在木工车间的大墙上,每天大家都要毕恭毕敬对其“早请示,晚汇报”的毛主席像,眼睛被人扎了!扎得还不轻,每只眼睛被小针扎了三个小窟窿眼!
包括来子在内,谁能容忍伟大领袖的眼睛被扎?
从那一天起,整个联社沸腾了,群情激奋了,李永存更加兴奋,他在紧急大会说:“以唯物论观点来看,好事和坏事是可以转化的,通过这件让人瞩目惊心的事件,给那些中间派,逍遥派和落后分子敲响了警钟!从此,联社阶级斗争的盖子就可以揭开了!”
专案小组进入了联社,召开大会,让大家踊跃揭发,凡是可疑的人和可疑的行动,都作为检举证据。最先是将那几个阶级敌人看管起来,集中学习,集中管理。进而重点追查类似来子一样的“可教育好子女”,逐个谈话,交待出半个月来的一切行踪。
这些日子,来子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皮麻。这是因为皮麻社又来了一个新人,叫张洪生,是一个老高中生,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没能上大学读书。张洪生原本在电厂工作,因为政治形势严峻,类似他这种出身的人,被清除重点工作单位,作为无业游民,被调配站介绍到了皮麻社工作。洪生倒底是有文化底子的人,谈今论古,天文地理,几乎无所不通,在来子眼里,张洪生几乎就是个落魄的博士。
洪生大来子十多岁,和洪生在一起工作,来子感到很愉快。 最让来子认识洪生的事情,是他和洪生坐对面割鞭梢的那三天,洪生用了三天时间,给来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《薛礼征东》, 来子不仅被传统故事吸引,更佩服洪生的口才和记忆力。
洪生向付师傅建议,说这种老式的手工刮皮革方式,不仅费力费工,还影响质量,应该做一个机械刮皮机,付师傅欣然同意了,并决定来子给洪生做助手。
洪生是能手,带领来子,画图,买材料,切割材料,焊接,洪生电气焊全会使用,还精通电路,没有多久,由洪生自行设计,来子做下手,一台电动刮皮机即将大功告成。
该着来子倒霉。就在这令人兴奋的时刻,来子出事了!并且是政治事件。
那天是个晴朗的天气,天空中万里无云,洪生在一边核对图纸,来子闲来无事,便拿起电焊防护镜对着太阳看了起来,1968年,正是太阳黑子爆发强烈的年份,来子在防护镜里看到太阳上有两个黑子,便喊洪生:“张哥张哥,你快来看,太阳上怎么会有两个黑点呢?”
洪生正在专心研究图纸,太阳有黑子,对他来说也不算新鲜事,洪生显得很平常地说:“那没啥呀,不稀奇,这是正常现象”。说过之后谁也没有在意,洪生和来子照旧在捣鼓刮皮机。
晚上,例行活动时,来子抱着手电筒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会场,找到一个地方坐下后,静静地等待节目开始, 他没有注意到气氛的变化。“万岁、健康”呼毕,传达一个什么文件后,照旧是李永存政治训话,一开始他讲的什么内容来子并没有在意。但接下来的话,就让来子脊背冒冷汗了:
“龙生龙凤生凤,老鼠生来会打洞,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!有些狗崽子,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反革命的本质,他仇视文革,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,他公然污蔑老人家身上有黑点!”
说到这里,李永存顿住话语,转过身来,把目光威严地盯在来子身上不动,来子预感大事不好,赶紧低下了头,避开李永存犀利的目光。
但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,只听得李永存提高声调,高声喝道:“把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,来子,揪出来!”
吓得面如土色的来子,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站起来,胆怯地走向地中央,还没容缓过神来,李永存便大声质问:“你个狗崽子!你老实交代,你为什么还要污蔑伟大领袖?”
来子赶紧争辩:“我没有!我没有!”
“你还敢抵赖?有证人证明,你还抵赖?”
随后,铁工社的张怀师傅站了起来,用手指着来子的鼻子:“小来子,你的话我听见了,在场还有张洪生,我冤枉你没有?”
来子张着嘴无言以对,张怀见状,像斗赢的蟋蟀一样,振臂高喊:“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子!”
下面人只好跟着喊:“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子!”
就在这紧张时刻,身为联社革委会副主任,皮麻社主任的付师傅从地上站了起来,边往前走边喊道:“停!停!”
付师傅走到地中央后,面对李永存大声说道:“小李子!我今天叫你一声李主任,咱们说话办事要摸摸良心,咱们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,来子今天确实说太阳上有黑点的话了,但他那是拿电焊镜看完后才说的,没有政治目的,我们不能无限上纲上线,来子小,还是个孩子,你这样做,不是让来子和他的家庭雪上加霜吗?!”
随后,付师傅又转过身来面对众人:“我说的对不对?你们大家给评个理”。
下面虽没有公开支持的,但点头的,交头接耳的人很多,气氛明显对付师傅有利。全场沉静了片刻后,李永存终于说话了:“那好吧,既然副主任都这么说了,来子下去吧!但必须把这件事作为教训,以后不得胡说!”
在付师傅的力挺下,来子逃过一劫。
追查针扎毛主席眼睛的案件有了进展,草织社的宋主任有重大嫌疑,理由是宋主任这些天来心神不宁,心惊肉跳,茶饭不思,没等别人过问,自己就喃喃自语“我没扎毛主席,我没扎毛主席······”。
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,在专案组过问他的时候,宋师傅一会说扎了,一会说我没扎!说法反复无常。
一天晚上,开会还没有散会,看管宋主任的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,结结巴巴地向在场的干部汇报:“不,不好了,宋,宋,自杀了!”
闻听此话,来子和众人一起涌向看管宋主任的房间,只见宋主任倒在地上,口中涌出大量黑色粘液,屋子里充满了酸臭味。身边倒着一个瓶子,人们拿到手里发现,瓶子里剩下的一半,是焊接用的硫酸。
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宋主任抬到两轮小推车上,来子和几个年轻人推着小车,奔向承钢医院,路上,宋主任口中仍旧往外涌出黑色粘液,散出酸酸的恶臭。
宋主任当天没有死,抢救过来之后,奄奄一息,几个月后才死去,宋主任死去后,究竟是谁扎了毛主席的眼睛还是迟迟没有结论,最后只好作为悬案,不了了之。来子私下里和几个小哥们研究过,都认为是李永存为了揭开斗争盖子,设下的苦肉计,但没人敢公开说出一个字。
让联社人最为兴奋的事情,莫过于每次“最高指示”的发表。每当白天广播喇叭预报:“今晚将有重要新闻播出”,大家便欢欣鼓舞地做好各种准备,除了锣鼓镲,还要预备高跷,彩带等多种道具。
“最高指示”发表的晚上,人们会早早地吃晚饭,然后聚集在联社院子里等候,当《新闻联播》开始乐曲刚刚响起,人们便按捺不住了,各处锣鼓震天响,秧歌队高跷队似长蛇阵一般涌向街头,老人家说了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民对伟大领袖发出的“最高指示”的态度,什么人,什么单位都不能也不敢落在后面行动,因为那是对伟大领袖忠诚度的体现。
来子很希望每天都有“最高指示”发表,因为他喜欢打鼓。刚开始的时候,是木工社的刘慧打鼓打得好,小刘打出的鼓点,有轻重缓急,有抑扬顿挫。来子对小刘的鼓艺十分赞赏,每当庆祝时,来子都会跟在小刘身边,观察他的打鼓的手法和技巧,几次下来后,来子也能在小刘双手疲软的时候,接过来敲打一番,再后来,来子已经独当一面了。咚 咚 咚 咚,枯燥的四个拍节,在来子手里,可以变化无穷,来子还利用鼓面中央和边缘位置不同形成的鼓音声调不同,敲打出不同韵味的声响。
平时在滦河街里的缝纫社,女人多,一般活动他们都是默默无闻,唯独在“最高指示”发表的时候,他们便成了主力军,扭秧歌,踩高跷,挥舞着手中的红色、绿色彩带,在窄小的滦河街上,展现着被压抑女人的妩媚。
因为“最高指示”都是在晚间发表,所以庆祝活动多大是晚间进行,但也有一次例外,那就是迎接“毛主席送芒果”。
宣传机关把毛主席送给首都工人的一颗芒果,说成是对全国人民的“最大鼓舞,最大关怀,最大教育,最大鞭策!” 全国各地人们当然要感受恩泽,没见到芒果没吃到芒果不要紧,被党教育出来的民众是聪明的,仍旧会表现出如同自己得到了芒果一样的感激之情,便做出无数个假芒果,用高级玻璃杯罩上,众人抬这假芒果游行。来子觉得,与其说是感恩,不如说借着这个机会大家凑凑热闹。
那一天,联社的人们,尤其是女人们,跟在假芒果后面,足足在滦河大街上扭了一天,来子也因为打鼓,双手几乎抡不动鼓槌。
狂欢时间持续最长,要数“九大”召开。伴随着“长江滚滚向东方,葵花朵朵向太阳,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,我们放声来歌唱”的歌声,李永存感觉形势越来越好,内心愈发的高兴,联社的人们也按捺不住内心莫名其妙的兴奋,至少,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,会让郁闷的心情在锣鼓秧歌中获得释放。后来的情况也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,从“九大”召开到闭幕,联社的人们有幸上街三次。
一次,发了工资后,来子照例将二十八元钱交到母亲手里,来子母亲看了一眼来子说:“给你五元钱吧!你自己去买一件喜欢新球衣”。
来子按母亲的吩咐,到百货商店里挑选了一件红色球衣,这是他从生下来穿得最好看,最得体的一件衣服。来子穿着宝贝球衣上班,刚好经过铁工社的烘炉,来子见张怀师傅正在为一个锻件熟火,所谓熟火,就是将铁块和准备夹心的钢材一起加热到融化状态,然后敲打在一起,这是一个技术活,来子很感兴趣,便站在不远处观看,张怀见来子在一边观看,又见来子身上穿了一件新衣服,就来了坏心眼,他将熟火的锻件对准来子,用锤子使劲砸下去,只见一片火星像散弹一样射向来子,来子躲闪不及,身上的新球衣被火星烧成了一片网眼。
来子见过张怀暴打阶级敌人的场面,知道他是一个仗势欺凌心狠手辣的人,不敢多言,便噙着眼泪到了皮麻社。付师傅发现来子哭了,便过来询问,来子含着眼泪向付师傅诉说了来由,付师傅听后,立刻火冒三丈,一反平日里的谦和,拉着来子的手,边走边骂:“什么玩意啊!欺负人家孩子,算你能耐?”
到了铁工社烘炉门前,付师傅拉着来子的手,指着张怀大声高喊:“张怀!你给我出来!”
张怀见怒气冲冲的付师傅领着来子前来兴师问罪,只好笑呵呵地走了出来,付师傅指着张怀质问:“你是什么东西?你真有能耐啊!人家孩子新买件衣服多不容易,被你烧成这样,你算人吗?你缺德不缺德?”
张怀狡辩道:“付师傅,我又不是故意的,谁让来子站在这看热闹呢?”
付师傅更火了:“你少胡说!都是手艺人,谁不懂这个?你熟火的时候,能不看看旁边有没有人,能不能伤人?”
在付师傅的力争下,张怀掏出了两元钱作为赔偿,这才拉着来子的手回到皮麻社,反过来训斥来子:“行了!别掉眼泪了!长点教训,那些混蛋的东西,坏心眼多着呢!以后少到他们身边去!”
来子父亲有历史问题,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,这两年经常被叫走,大会小会批斗或陪斗,直到不能下床,才免去被批斗的厄运,但身体也彻底垮了下来,六九年夏天周日的一个早上,来子的父亲死在了家里。
作为黑五类,没有人敢靠前帮忙,五方六月的大夏天,来子父亲到了中午还没能抬出房间,肚子已经鼓胀起来。来子想到了付师傅,付师傅得知后,立即做出了安排:先是找人去木工社,赊欠一口半成品的白茬棺材,又吩咐人到商店买了两瓶红墨水,将白茬棺材涂成红色,接着,又调集不怕政治粘连的,在联社集中学习的黑五类们,来到来子家,并安排自己的弟弟,亲自为来子父亲擦洗面孔,穿上衣服,最后让黑五类们抬着来子父亲到山上掩埋。
九大召开后,李永存等人更加得志。不知为什么,李永存对来子总是看着不顺眼,甚至当面向付师傅提出,希望皮麻社辞退来子这个出身不好的“狗崽子”,但每次都被付师傅拒绝了。来子清楚,小皮匠职业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,总有一天,自己会离开联社,离开付师傅。
六九年的秋天到了,原本青青的树叶,被无情的秋风扫到空中,再飘落到地上,来子预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滦河街道派人来到了联社,告知联社领导,来子属于六九届毕业生,按规定在上山下乡范围内,联社必须先将来子辞退,然后街道再考虑他的去向。
离开联社的来子,辗转到了远远的地方,他想念联社,怀念当年的小哥们,便给老实厚道的侯哥写了一封信,但他没有想到,就是这封信,暴露了他所在的地区和单位,若干年后,在清理个人档案时,来子才得知,档案里竟然有联社革委会发来的信函,内容是:该人出身有问题,希望有关单位谨慎使用。
若干年后,来子回到了承德,但他早已对李永存淡漠,也懒得打听关于他的情况,只知道当年红极一时的他,后果似乎不太好。至于付师傅,来子不会也不敢忘记,因为,那是他当年的师傅,也是他家的恩人。